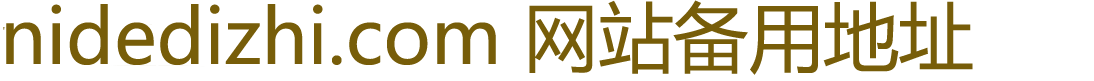
Swallow/2
,很快消失在镜子后。唯剩一旁叶贝门清风拂过,紫竹坠摆。
&esp;&esp;花厅西晒,沐浴在清净里。
&esp;&esp;签好最后一份手续,江猷沉站起,陷入角落的磨砂牛皮沙发。
&esp;&esp;余光里一个纤小的绿影,踏踏脚步,跑过长窗,第一到第六扇……影子不见了,脚步是兀地消失的。
&esp;&esp;“叩叩”,正门以熟悉的频率敲响。
&esp;&esp;江猷沉回首前,先听出是王瑛沛。男人变得清醒而警觉,点头如恭请坤安。
&esp;&esp;王瑛沛只把自己一个分公司交给儿子打理。他的行程看似十分混乱,实则一丝不苟,不为谁更改。
&esp;&esp;对话走向结束之际,王瑛沛只赞赏他做事措置有方,却没慰问儿子心情。
&esp;&esp;江猷沉面上就看出心事多多,作为母亲,她心里知道,多少和近来南京申府与江鸾通讯越发密切有关。
&esp;&esp;毕竟过去这些年,他好不容易靠着照顾妹妹,获得了一点小家庭的归属权——他曾丧失过这种归属权。
&esp;&esp;王瑛沛亮了声气叫他正名,知会一句:“早些来大厅。”不管什么他有何理由,比如什么不去影响妹妹做主人公。
&esp;&esp;至于室外,太湖石前的江鸾,王瑛沛则按住办公桌,头偏向她道:“行李收好了?”是温笑着问江鸾。
&esp;&esp;她对女人捣捣头,消失在假山后,仿佛可以随时飞去檐角当一只瓦猫。
&esp;&esp;虽然,她已在那无声盯着王瑛沛和江猷沉不知多久。
&esp;&esp;再没其他人步入花厅后,像苑画铺陈开来那样,卷轴一路滚到尽头,瘦皱漏透的太湖石假山旁,现出一个小小的人。
&esp;&esp;她的无袖绿蓬纱上衣,系带是环绕脖颈一圈,到左肩系出一只蝴蝶结,仿佛可以压下她纤薄的肩。
&esp;&esp;此刻,窄而长的长窗,江鸾出现在最中,直勾勾盯江猷沉。
&esp;&esp;锻光芭蕾运动鞋,在木门槛上摆荡了一会儿。泠凉的双臂才折落下来了,相仿猫,越过长窗,迈步进花厅。
&esp;&esp;沙发另一头前摆了箱长鱼缸。一方浅蓝的水囿软禁金鱼,火苗一样的橘红点点闪摆。
&esp;&esp;她的双膝跪到靠墙那只沙发上,推开棱形窗。棂条组成的格心,镂透光影落她肩膀,洇得光色成了过期淡奶油,涂抹到雨露沤过的麻布上。
&esp;&esp;“刷啦”,一只沾丙烯的纸质小刀飘出窗。掠过地砖,一路飞去。
&esp;&esp;鱼缸里的金鱼开始逃窜,原来是半挂窗棱的一条猫忽然撑起,跑出门去。
&esp;&esp;紧接着,小窗外昏睡的荷塘边,传来警卫员的交谈,饱盈笑意地,为她捕捞那只游弋的纸小刀。
&esp;&esp;再回室内,他在小憩。他西裤的褶皱像笑纹,现在这些笑纹也在松弛中落下,随它的主人陷入沙发,彻底消失在一片僻静的黑色阴影里。
&esp;&esp;至于西装外套,早被江猷沉随意掷在沙发靠背。
&esp;&esp;他五指抵饱满的额,盖住了半边脸,长睫阴影落颧骨上,侧身都隐于金黄光线中。
&esp;&esp;江鸾玩够了,才坐到沙发扶手上。
&esp;&esp;——多像是无心选中,才离他如此近。
&esp;&esp;她俯视江猷沉几秒,悬着的小下巴带着点儿冷弧,渐渐,某种默允如福至心灵——
&esp;&esp;躺到他丰裕的大腿上,她双手交盖肋骨上,拢闭眼睫。这时候低头看她,就像站灵柩外,朝里看去——出其不意不过一具熟睡的艳尸。蕾丝裹尸布由她的肌肤绣成。
&esp;&esp;江猷沉将脸偏了偏,抵着额的手指却落下了,轻轻拂过她头顶。在柔和的傍晚光辉里,只为望她而垂眸。
&esp;&esp;公司、集团、分部,几百个下属……永远处理不完的烦心事。
&esp;&esp;江猷沉将她手臂托起,将她从后抱怀里,还要拦住她的腰,直到下巴轻轻悬她肩上,在妹妹面前获得片刻喘息。
&esp;&esp;男人镇定的鼻息若有若无,抚她肩颈的光裸肌肤。起了痒意,她有些逃避地耸高点儿薄薄后背,却使他感触出一番,江鸾的无私馈赠来。
&esp;&esp;有力的前臂轻轻往后拢她的腰腹,隐秘地占有她的肚脐。
&esp;&esp;他的搂抱格外轻,像在扮演童话书里某个不掺情欲的守护骑士。
&esp;&esp;江鸾觉得这个姿势不舒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