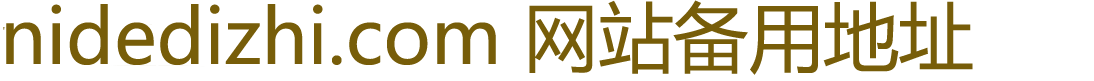
第90章:潛影尋蹤
苏清宴举着火把,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地道里快步走着。火光一跳一跳的,把他细长的影子在粗糙石壁上扯得忽长忽短。空气里有股血腥味混着泥土的潮气。血跡断断续续洒在地上,成了唯一的路标。他不敢大意——伏魔金刚指有多狠,他自己清楚,但那头领能在这种地方盘踞这么多年,肯定不是省油的灯,得防着点。
地道不算深,走了大概百来步,前头忽然开阔了。一个更大的洞窟露了出来,一扇厚石门半开着,门缝里卡着个人,正是那黑道首领。他面朝下趴着,身下一大滩血在火光里泛着暗红的光,已经没动静了。
苏清宴戒备着靠过去,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那人的腿,没反应。蹲下身探了探鼻息,又把人翻过来看伤口——指劲从后心穿进去,肺腑贯穿,大动脉直接震碎了。看样子,这傢伙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想推开石门逃命,结果血流太多,力竭而死,倒在了离生路一步之遥的地方。
“总算没让他跑掉。”苏清宴松了口气,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要是真让这人逃了,把自己的行踪漏出去,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他起身把尸体拖出去草草埋了,接着折回地道,仔细检查了各处机关。座椅底下那个入口被他重新封死,沿途能找到的暗门也一一合上。这啸云寨地势隐蔽,密道错综,说不定将来哪天能用上。
处理完这些,他摸出师爷译好的那份奏摺,对着上面的地址,悄无声息地潜向完顏娄室的大营。
夜沉得很,金军大营却灯火通明,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森严。苏清宴伏在远处一棵大树的枝椏间,藉着叶子缝隙观察。整个营地外围,居然新竖起了一圈铁栅栏,足有七八尺高,上头还蒙着厚铁皮,严严实实的,只留了几个由重兵把守的出口。这哪像军营,分明是个精心打造的大笼子。
“笑傲世,果然是你。”苏清宴心里冷笑。这种劳民伤财、画蛇添足的搞法,绝不是完顏娄室一个打仗的将领能干出来的。除了那个多疑又爱算计的笑傲世,他想不出第二个人会这么处心积虑地防着自己。
他身形一动,从树梢飘然而下,落地无声,随即贴着地面疾掠而出,藉着营帐投下的阴影一路穿梭。动作快得像夜色里的一道鬼影,接连避过了好几队巡逻兵。他没急着找陈彦康,而是先把整个大营的佈局摸了个遍。
最后,他的目光定在了营地正中一座被严密看守的帐篷上。帐篷周围站着七八条汉子,个个太阳穴鼓起,气息沉厚绵长,一看就是内家好手,绝不是普通士兵。苏清宴几乎能断定:陈彦康就被关在这里头。
“硬闯不行。”他立刻打消了强攻的念头。这些高手只是明面上的,天晓得笑傲世和笑惊天两兄弟是不是就藏在附近哪个角落,等着自己往套里鑽。一旦被围上,别说救人,自己脱身都难。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蠢事,他绝不会干。
现在,唯一的武器就是耐心。
苏清宴悄然后撤,几个起落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。他回到了啸云寨那处地下密室——这儿成了他眼下最理想的藏身点和据点。
接下来的日子,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和观察。每天深夜,他都会潜入金军大营一次,每次都只远远看着,记下守卫换岗的规律,寻找那铁桶般防守的缝隙。可几天过去,营防依旧滴水不漏。苏清宴倒不着急,他有的是耐心——再严密的佈置,时间久了,总会有松懈的时候。
蛰伏的这段时间里,他想起了黄裳赠他的那套完整内功心法。之前一直东奔西跑,没静下心来细琢磨,眼下正是机会。于是白天,他在密室里潜心修炼;夜晚,便化身暗影,窥探着完顏娄室的大营。
那心法确实博大,直指武学根本。苏清宴本来底子就厚,这一练,只觉得体内真气流转的路径发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变化,变得更圆融,更生生不息。更让他惊喜的是,这心法对内力损耗后的恢復有奇效——就算有一天内力尽失,照这法子练,叁四个月也能全数回来。
“黄兄真是……惊世之才。”苏清宴心里忍不住叹,“不光是文曲星下凡的状元,于武学一道,竟也是开宗立派的人物。能得他和宗剑师父的绝学,是我苏清宴走了大运。”
时间一晃,两个多月过去了。
果然如苏清宴所料——再紧绷的弦,也经不起这种漫长无声的消磨。金军大营的戒备,在日復一日的平静里,渐渐松了下来。而最先绷不住的,是笑傲世。
中军大帐里,气氛有点压人。
完顏娄室坐在主位上,一张国字脸阴得能拧出水。他重重把酒杯顿在桌上,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“笑先生,你口口声声说那石承闻重情重义,一定会来救他宝贝徒弟。现在呢?快叁个月了!鬼影子都没见一个!”
站在一旁的陆万象赶紧躬身:“将军息怒,一切都在我师父掌握之中。”
“掌握?”完顏娄室像听了个天大的笑话,猛地站起来,“掌握就是让我几万大军在这儿乾耗着?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!你知道这两个多月、接近叁个月,吃了我大金多少粮草、多少银子吗?早知这样,我还不如直接让那小子找他爹要钱来得实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