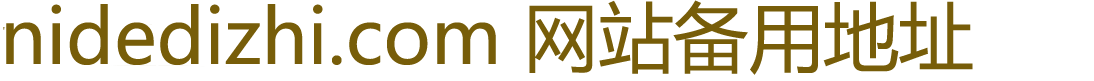
59:诀别信——一别两宽各成风景
崔府书房内,沉水香燃至半寸便萎了,烟灰簌簌落在青玉笔山凹处,积成化不开的愁云。崔愍琰指节抵着眉心,目光锁在案头那封已拆的密信上——怡亲王的笔迹,九个字如冰锥:“事已成,叁日后,凝水居。”
他指尖无意识摩挲着信尾的火漆印,那是怡亲王府独有的青鸾纹。按太子的阴损性子,这“套”他本不该钻,太子称病宿在府邸月余,上朝巡视皆托下属,圣上早派暗卫盯着,此刻却答应了他的邀约,遣人递信给他,绝非吉兆。可“事已成”叁字又透着蹊跷,像块悬在蛛网中央的饵,明知有毒,却勾得他生出几分玩味。
沉水香熄了,只剩一缕残烟在烛火下扭曲成灰。童舟捧着新沏的君山银针,指尖因紧张而发颤,茶盏边缘溢出的水痕洇湿了袖口。他偷眼觑着案后之人,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不安定,此刻,崔愍琰指节抵着眉心,玄色锦袍下的肩背绷得像张满的弓,烛火在他瞳仁里跳得厉害,像即将燎原的火。
“说。”崔愍琰的声音比冰还冷,尾音却带着不易察觉的颤。
童舟喉结滚动,声音压得几不可闻:“回大人……探子来报,青玄子昨日给太子诊脉,说‘仙缘将至’,太子赏了叁锭金子。只是……他总打听南塘的事,问小姐的病症可有好转,说、说小姐同太子一般,皆带着苑氏一族的弱症……”
“说重点。”崔愍琰突然抬眼,目光如刀,童舟吓得一哆嗦,差点摔了茶盏。
“那老混账说……说要让小姐的身子来试他炼的丹,以毒攻毒,放血给太子炼药引……”童舟说到最后,声音已带了哭腔,“那江湖术士竟说‘崔小姐的弱症血,正合太子体质’,简直荒谬!”
“砰!”
紫檀木案上的青瓷茶盏被崔愍琰生生捏碎。瓷片扎进掌心,鲜血混着茶水淌在案上,他却浑然不觉。烛火被他骤然爆发的气势逼得摇曳不定,映得他眼底猩红一片。
“以毒攻毒?”他低笑出声,笑声却比夜枭啼叫还瘆人,“苑氏弱症是胎里带的虚,放血便是剜肉补疮!那太子命不久矣,便想拖着我音音垫背?青玄子这老匹夫,当我是死的?”
童舟吓得跪倒在地,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:“大人息怒!小姐在南塘养病,有夫人照看,还有侯爷旧部守着,太子他、他动不了……”
“动不了?”崔愍琰猛地起身,玄色外袍带起一阵风,将案上密信扫落在地。他一脚踹翻炭盆,火星子溅在他袍角,他却像感觉不到烫。
“怡亲王说‘事已成’,怕不是指湘宁布局太子愿意见我;是指他东宫已算准我会为音音妥协!不敢不去湘宁!东宫这病秧子称病月余,圣上早有疑心,此刻递信邀见,不就是要拿音音做筹码,逼我入局,怎么?我若不见他敢不从他东宫,他就要请旨去南塘抓人?”
男人抓起案头那柄镶玉匕首,指腹抚过刃口,那是崔元徵在南塘时送他的,赠与他护好自己。此刻匕首映出他扭曲的脸,眼底的怒火烧得他理智尽失:“想拿音音试药?做他的春秋大梦!我崔愍琰的妹妹,是给个废人当药渣的?”
童舟爬起来,抖着手去扶他:“大人,您的手……”
崔愍琰低头,见掌心瓷片扎得血肉模糊,却嗤笑一声拔出碎片,随手扔在地上:“这点伤算什么?比起音音若真被抓去放血,这点疼算个屁。”他望着窗外漆黑的夜,眼底的猩红渐渐沉淀成冰,“太子不是爱试探么?我便让他探个够。”
男人冷笑。
青玄子是怡亲王给太子寻的“神医”,他虽然不知此人到底有何奇技淫巧能俘获太子信任,但自他入府,太子便坐实“昏庸求仙”的人设,美其名曰“闭关炼丹”来看,此人却有几分小聪明资质,但这小聪明要是敢动他的人,那就休怪他翻脸无情。
“他以为我是头号嫌疑人,就该乖乖躺到案板上任他剖。”崔愍琰将茶盏重重一搁,青瓷与紫檀木案相撞,发出脆响,“却忘了谢惟渝不在京内,正是清剿他那些暗桩的时机,真是蠢物,威胁我?他也配。”
窗外忽起风,卷着雨丝打在芭蕉叶上。他想起叁日前收到的密报:谢惟渝在联络旧部,似有“清君侧”之意。
“童舟,”崔愍琰忽然起身,披上玄色外袍,“备两份拜帖,一份给怡亲王府,说‘叁日后必至’;一份让那暗桩寻机会递到青玄子手里。”他指尖拂过腰间玉佩“就说我‘夜梦仙师’,挂心病妹,想请他过府一叙‘长生诀’。”
童舟一怔:“大人要……”
“他要演昏庸,我便陪他演到底。”崔愍琰望向炭盆里未燃尽的信纸,火星明灭间,映出他眼底的冷光,“太子不是爱试探么?我便让他探个够——探探我到底是‘棋子’,还是能掀翻棋盘的人。”
崔愍琰不傻,太子那人既然敢让以崔元徵做药引的消息传出来,为的就是让他上勾,那他岂有拂了太子美意的道理。
童舟会意,忙取来素白拜帖。崔愍琰执笔蘸墨,笔锋在纸上悬停片刻,忽而冷笑:“给青玄子的这封,要写得‘情真意切’。”他指尖在“病妹”二字上虚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