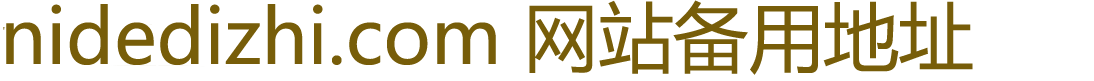
127前往学校
虞峥嵘提前到校为军训做准备的时候,虞晚桐也没闲着,她被选为军医大这届本科新生的发言代表,这几个晚上都在写发言稿。
这对她来说并不困难,但对着电脑啃笔头的行为还是给了她一点紧迫感——开学将近的紧迫感。
为了不在军训里挂得太难看,她上次度假回来就开始跑健身房,最近来了上海也没落下,直到报道前几天才没约私教。
她怕练过头了恢复不过来,到时候肌肉酸痛反撑不住军训就不好了。
军医大的报道时间要比沪师大早一点,因此虞晚桐不必操心退房的事情,直接拉着她的行李去学校报道就行。
柳钰恬依依不舍地“抹泪”告别,并且承诺会好好善待她这些天的购物成果——指打包发快递帮她寄回京市。
“那就靠你了。”
虞晚桐郑重地将手合在柳钰恬掌心压了压,换来柳钰恬一句同样郑重的“保重”:
“你一定要从军训里活下来,两个月之后我会带着美食去收尸、啊不探监的。”
虞晚桐一听她那做作的语调,就知道柳钰恬是故意的,故意逗她,冲散一下离别的忧愁,也减轻一下她“赴死”的心理负担。这份好意她心领了,但是这么不吉利的话下次还是别说了。
于是她勉强忍住翻一个大白眼的冲动,没好气地道了声:“知道了,我走了。”
报道需要的证件材料虞晚桐早已整理好封在文件袋里,林珝帮着她点过,确定是没有疏漏的。
至于行李,她和柳钰恬来上海时各自带了好几个行李箱,其中一个就是专门开学后用的,里面的换洗衣物以及护肤品什么的都是整理好的,直接拎着走就行,剩下的行李箱直接快递发回家。
虞晚桐是坐地铁过去的,越靠近翔殷路,拿着行李坐地铁的年轻人就越多,一看就是和她一样,去海军军医大报道的新生。
虞晚桐的目光浅浅落在他们身上,略带着些许好奇。
这些新生中大部分都是玩着手机乘地铁,有个别结伴而行的在交流,剩下的一小部分则是和虞晚桐一样,亮着眼睛四下打量,区别只在于打量的隐晦程度和目光热烈程度。
虞晚桐只看了几眼就将目光收了回来,然后在手机上给哥哥发消息:
【干饭小虞:“哥我在去学校的地铁上啦~”】
虞峥嵘没有立刻回她,军训期间教官们的手机也受到严格管制,只有在个人支配的活动时间才可以使用。
临近开学与军训,虞峥嵘要开的会,要处理的工作并不少,虽然不像之前在部队那样基本只有晚上才能回,但基本上都延后得厉害,秒回更是不必想了。
虞晚桐早就习惯了,这是虞峥嵘的工作性质决定的,而她和虞峥嵘的兄妹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绝不会像普通情侣那样,因为一条或几条消息回得慢了,就滋生出惶惑不安。
被坚定地爱着的人是不会焦虑自己究竟是不是被爱着的,因为爱有回声,爱有留痕。
任何的不安全感都不是空穴来风,总会有那么一个、两个主控上忽略的细节被潜意识捕捉到,继而抽丝剥茧,犹疑在“他是否真的爱我”的疑问中。
虞晚桐和虞峥嵘不会。
他们爱得不留余地,所以他们之间没有足够引发猜疑的距离。
他们不是福尔摩斯和罪犯,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摊开在阳光下询问,没有你追我逃的猫鼠游戏。
他们不是福尔摩斯与华生,因为他们中任何的一个都不占据绝对的优势,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绝不会愿意永远屈从于另外一个,仰赖对方或出于经验,或基于天赋的教导。
他们是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,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他们势均力敌,了解对方胜过了解自己,无论是爱还是恨,心跳永远为对方跳得最快。
他们了解彼此的光鲜亮丽与狼狈不堪,知道如何能够刺痛对方的心灵,却又默默在每一个刺痛对方的夜晚默默守护对方的人格与尊严。
他们总是试图将对方拉进自己的世界,用自己的规则去约束对方,却总在为对方破例和让步。
他们深知彼此的特别与不同,却无可抑制地被对方吸引。
他们并非完美之人,各有各的残缺,尖锐而冷刻,但当他们在一起时,残缺嵌合,肌肤的温度融化灵魂,铸出一轮满月。
当他们为同性时,这轮满月叫做“宿敌”。
而当他们为异性时,这轮满月叫做“欢喜冤家”。
而当他们既为异性又为兄妹时,这轮满月叫作——
灵魂伴侣。
和命中注定的哥哥与爱人比起来,其他异性都显得那样单调乏味。
就像围拱在月亮周围的星辰,你知道它们在亿万光年外闪耀得如同太阳,但你却连问一问你们之间到底有多少光年的距离都懒得。
更何况虞晚桐自己本就是一轮太阳。
虽然稚嫩,但已足够耀眼。
虞晚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