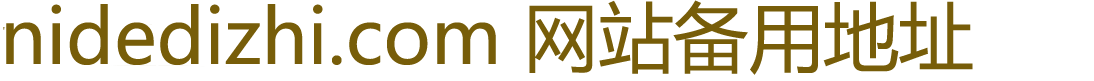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章释怀(影山车)
在昂贵的地毯和木制的地板上划出一道狼藉,这是个锋利的界限。
“够了!”
她不想再见到他。
扔在地上的高尔夫球杆还沾着血,几分钟前还有某个得意洋洋的女人狗仗人势,她即将被送出国,在这个自称最受宠的女人眼皮子底下。
她看也没看,顺手抄起身边茶几上仅存的一个水晶杯,猛地砸在了两人之间的地板上,刺耳的碎裂声炸开,晶莹的碎片迅速飞溅开来。
“我和你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,你看看这里,看看周围,是我想错了”,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理解自己。
淅淅沥沥的雨夹雪落下,本就寒冷的天气更是低了温度,天色沉沉。
斋藤春奈就站在这片混乱的中心,她还穿着音驹的校服,看上去似乎一切如常。
可那天怎么就情绪上头了呢,打着为赤苇的借口,说出了伤害人的话。
此刻的她,与木兔记忆中任何样子都不同,陌生而危险的气息弥漫开来。
正因为他这不合时宜的出现、不合时宜的质问,他们之间那本就谈不上深厚、哪怕再有轻松愉悦的友谊,于此刻伴随着这声碎裂彻底崩解。岌岌可危,再无转圜可能。
“只是觉得赤苇可怜?只是觉得我冷酷无情?你觉得我对不起他,对,是,我是做了,所以呢?你懂什么?你以为你是谁?”
就在几分钟前,这里刚结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手臂上的血还在流,这是被那抬出去的女人伤的。
而将流血的手暂时藏在身后的斋藤也没有料到,进门后的木兔说出的会是,“春奈,你不应该和赤苇分手,你知道他最近”。
“别再装好心了”
“没有人能替我做决定,想死的都可以试试”
木兔的心猛地一沉,强烈的慌乱和后知后觉的不安攫住了他。而视线也终于看见了斋藤的不对劲,担忧的语气快速,“你受伤了”。
心沉入谷底,斋藤的视线掠过木兔,又扫了一眼满室狼藉的周围,最后落回他的脸上。终于,嘴角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弧度,声音干涩而平静,“你也是来指责我的,对吗?”。
有位自恃身份、前来规劝兼示威的家族长辈,带着不怀好意的礼物和说客,还有她讨厌看见的那些小三。
凭什么她要这么生活,为什么她要离开,斋藤质问的似乎不只是木兔。
沿着滴沥沥的血点,穿过错落景致的院子才看见客厅的混乱。一路上都是穿西装的保镖,沉闷死寂的氛围,所有人都带着面具般压抑。
——可他本应该注意到的,注意到这绝非寻常争吵或玩闹后的场景,注意到少女周身萦绕的那股几乎实质化的暴戾与疲惫。
灯光晃过,木兔甚至看到了滴落在石阶上的、尚未完全凝固的暗红色痕迹。
“你以为所有人都可以像你这样,只需要考虑简单的爱好吗?”
他们都太着急了。
“凭什么要来干预我的选择,凭什么——”
在她祖母刚去世,尸骨未寒之际,这群宗族亲人迫不及待地前来觊觎遗产,逼迫她交出股份。
屋内斋藤是在上野的提醒下才知道木兔来了,现在再收拾,显然已经来不及了,一整天的应付与反抗,她已然疲惫。
可还是在那天晚上去了,彼时屋里正发生过热闹。斋藤家坐落于一片幽静的富人区,还没靠近,木兔就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。
这一刻她眼神是陌生的,木兔甚至后退了一步。
于是按捺住的理智忽然断了,她抬手,制止了木兔的后话。
天真到让人羡慕,讨厌。
“别再来找我了,离开这里,别再出现了”
连她血缘上的父亲,也隐在幕后意图分一杯羹,他们拿定了她无所依靠。
那些玻璃碎片冰冷尖锐,映照着混乱的灯光,将两人彻底隔开。
她到底在奢望什么。
知道,他是没有立场的。
几个看起来像管家或律师模样的人正低声而快速地说着什么,与木兔擦身而过,客厅很快只剩下他们两个。
斋藤由着研磨将她送回家,去的是某处套房。今晚并没有约人,索性也没去
他们警惕地打量着他,但或许因为他穿着校服,又或许是得到了什么指令,并未阻拦。
一辆救护车闪着灯停在门外,穿着制服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匆匆进出,上面躺着一个个看不清面目、但显然伤势不轻的人。
极致的愤怒与荒谬感冲垮了斋藤的理智,少女选择用最直接、也最激烈的方式回应——她抓起手边的球杆,用暴力搅浑了这虚伪的谈判桌,也彻底撕裂了表面和平。
头昏脑涨,斋藤本不应该再见人,却还因为上野一句木兔好像很着急,让对方进了门。
斋藤打断他,向前逼近一步,被踩到的碎片吱呀作响。她身上的血腥味和那种冰冷的气势扑面而来,木兔连劝对方小心都来不及。